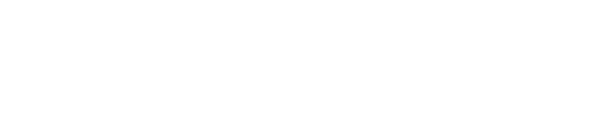鲍则岳 (William G. Boltz), 美国人, 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教授, 著名汉学家, 师从卜弼德 (Peter A. Boodberg, 1903-1972), 在出土文献, 古文字, 汉字理论等多个汉语汉字学领域研究深⼊, 成果丰富。 鲍则岳的汉字研究著作, 除了有“Early Chinese Writing (≪早期汉字≫)” (1986, 1996), “Language and Writing (≪语言和文字≫)”(1999),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in China (≪中国书写的发明≫)” (2000), “Phonographic Motiv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Comp oun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ase of wu武 (≪合体汉字形成中的表音动机:以‘武’为例≫)”(2006), “Pictographic Myths (≪象形神话≫)” (2006), “Orthographic Variation I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早期汉语书写文本中的 正字变异≫)” (2009), “Literacy and the Emergence of Writing in China (≪读写能⼒与中国文字的出现≫)” (2011) 等论文之外, 其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专著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一书中。 目前此书还没有中文译本, 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观汉记:⻄⽅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将其译为 ≪中国书写系统的起源及演变≫1), 本文暂译为 ≪汉字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夏含夷认为, 鲍则岳写作此书的缘起是以卜弼德为代表和以顾⽴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为代表的 两个⻄⽅学派对汉字性质的争论2)。 “鲍则岳是卜弼德最后的学生, 完全接受了卜弼德的文字学理论。 他在许多 文章里提到这些理论, 但最成熟, 也是最极端的论述, ⻅于 ≪中国书写系统的起源及演变≫一书里。”3)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 鲍则岳对汉字的观察和思考集中在两个大的⽅面:第一, 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的汉字 系统的起源和形成;第二, 汉字在秦汉时期所进⾏的发展, 改革和标准化工作。 下面, 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简 单介绍和相应的评价。4)
Ⅰ. 从“前文字 (forerunners of writing)”到“文字 (writing)”
1. “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对应物”
要探讨汉字的问题, 首先要从它的上位概念“文字”谈起, 即文字是什么。 大多数学者给文字下 的定义都是“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这一定义其实是从两个角度入手的:第一, 文 字是一种视觉符号 (visual signs), 这种符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第二, 文字的功能是用来交际 (the act of communication), 即记录语言。 由此, 可以得到如下的类比关系:
如果承认这一类比关系, 就要承认任何视觉符号及标志都是可以传达意义的, 比如药瓶上提 示“有毒”的标志, 禁烟的标志, 救护车上的红十字标志等等。 但是, 如果认为这些标志都是文字, 就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将文字定义为“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对应物”这一初衷。
2.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第二性的符号系统
很多时候, 学者们会说“文字的目的是表达思想”, 鲍则岳认为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文字的功能是 准确表达这种文字记录的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 (the function of writing is precisely to communicate what is communicated by the speech that the writing represents), 也就是说, “只有那些意义是由语 言来传达的视觉符号” (visual signs the meaning of which is mediated by language)才是文字。 换 言之, 表达思想的机制是语言, 文字是代表语言的, 文字的交际作用是这一事实的附属产物, 即文 字是记录语言的第二性的符号系统。 上面所提到的各种标志都是直接表达思想含义, 并且这种含 义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但这些含义都不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 因此, 这些标志都不是文字。
3. 文字是一种必须要有表音成分存在的视觉符号系统
任何语言都有词和语素, 语素是一种语言中最小的意义单位, 而词由一个或多个语素构成。 无 论有没有书写形式 (文字), 任何词都由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组成。 如果把词的声音称作它的“语 音方面” (phonetic aspect, 简写为P), 把词的意义称作它的“语义方面” (semantic aspect, 简写为S), 有书写形式的词, 将其视觉符号或标记称作“图像” (graph)。 无论一种图像是不是文字, 我们都可 以将声音和意义称作这种图像的“区别特征”, 这样, 借用语义学的义素分析法, 三者之间的组合 关系就有如下四种:
类型 (1)图像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意义, 它们仅仅是一些随意的刻画。 类型 (2)图像有意义没有 声音, 前面提到的药瓶上的“危险”标志, 禁烟标志, 红十字标志等即属于此类。 类型 (3)是一个图 像表达一个词。 类型 (4)是一个图像只表达声音, 不表达意义。
文字是代表语言的, 所以, 判断一种“图像”是不是文字的时候, 声音特征是一项核心的, 必不 可少的特征, 即这种图像类型必须是[+P]的。
然而, 图像记录词却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 图像记录的是声音 (G-P link), 即表音文字; 第二种, 图像记录的是意义 (G-S link), 即表意文字。 在后来的发展中, 表音文字的意义成分被不断剔 除, 表音文字的音仅仅代表某个音节的读音, 这一过程鲍则岳称之为“去语义化 (desemanticization)”。 也就是说, 文字是一种必须要有表音成分存在的视觉符号系统, 只有类型 (3)和类型 (4)两种文字, 类型 (3)就是表意文字, 类型 (4)就是表音文字。
4. “前文字”与“文字”的关系
明确了文字的定义, 将文字与前文字区别开来就容易了。 只有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语言的书 写符号才能被认为是文字, 即它必须是有语音的 ([+P])。 有些图像是只有意义 ([+S])没有语音的 ([-P]), 一般认为是这些图像逐渐进化和发展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字, 这些只有意 义没有语音的图像就是“前文字” (forerunners of writing)。 即, 鲍则岳所说的“前文字” (forerunners of writing)与“原始文字” (proto-writing), “初期文字” (embryo-writing)等术语是有区别的, “前文 字”并不是原始文字的一种类型, “前文字”还不是文字。
王宁先生 ≪汉字构形学导论≫在谈到“前文字现象”时说:“文字的起源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前文 字现象’可以算在文字起源阶段之中, 而严谨的文字学家认为, 只有证明了一批符号已经具有了音和义, 并用来组成言语, 才能确立为文字起源的下限。”1) “表意文字的形是直接从物象上获取的, 但必须与语 言结合有了音和义才是文字。” “一个仅有意义而没有语音, 不以语词为基础的形象不是文字。”2)
可见, 一个严谨的文字学家在定义文字, 划分文字与非文字的界限时应该是要慎之又慎的。 但 是, 直到现在依然“有人认为, 表音文字是对语言的记录, 而表意文字则是对事物的直接摹写, 是 可以脱离语言而存在的。 甚至有人否认语言先于文字的事实, 以致引发出‘汉字比汉语还容易学’ ‘可以不学语言先学汉字’的结论”。3)
Ⅱ. 汉字的性质
1. 将汉字定义为“表意文字 (ideograph)”带来的两种困惑
明确了文字的定义, 以及“前文字”与“文字”的关系, 也就可以给汉字定性了。 汉字是表意文字 (ideograph), 但是, 鲍则岳提醒我们, 这一主流观点容易给一些人造成两个方面的困惑。
困惑一:汉字是表达思想的。
汉字是表意文字 (ideograph), 但是 “ideograph” 的词根 “ideo-” 在西方语境中往往与 “思想” “意识”等概念有关, 有人因此认为汉字与语言无关, 只与思想有关, 他们甚至认为, 汉字存在一个 独特的书写系统, 很多对汉语一无所知的人也可以理解这一系统。
鲍则岳认为, 这种困惑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依然存在, 这种困惑的来源其实是这些人误解了 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汉字是代表词的, 不是代表一个个的声音的。 词不仅有声音, 更重要的是 有意义。 很多别的语言也借用汉字来书写, 和拼音文字不一样的是, 汉字在被其他语言借用的时 候, 借用行为发生在“词”的层面上, “词”的层面是不止有声音而一定要包含意义在内的。
语言是由词来表达的, 词是由文字记录的。 在这一点上, 汉语与拼音文字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 于汉语来说, 词是由汉字构成的, 在很大程度上, 汉字可以说是代表汉语的组成要素。 这里有一 个表达层面的问题, 汉字表达汉语 (语言/言语)是在词的层面, 拼音文字的字母表达它们的语言 (或 言语)是在声音的层面。
从有可能存在的表达层次来说, 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文字除了有表词文字, 表音 (音位)文字之外, 还可以有表音节文字。 现实生活中, 这三种文字是比较普遍的, 而记录语言的层 次超过词这一级的文字系统是十分少见的。
困惑二:汉字是表达概念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 汉字在很大程度上与语言无关, 汉字是表达概念的。 鲍则岳认为, 汉字在最初 的时候可以认为是表达概念的, 在这一阶段, 人们不需要了解关于汉语的一些必要的知识也能理解 汉字。 但是后来汉字逐渐发展, 人们必须通过汉语, 通过有关汉语的一些必要的知识才能理解汉字。 这些人之所以不能正确认识汉字的性质 (或者说一切文字的性质),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否定了 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文字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语言 (Writing is, in its turn, a spoken thing)”。
鲍则岳认为, 产生上述两种错误观点的关键在于, 汉字是将一个词的读音整体呈现的, 而拼音 文字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单独呈现的。
2. 汉字是“表词文字 (logograph, lexigraph)”
在本书的introduction部分, 鲍则岳就引用了Du Ponceau的观点, 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词的, 同时也是用来表达汉字书写者的独特思想观念的。 所以, 从性质上来说, 汉字与拼音文字一样, 都 是用来记录语言中的词的, 只是所用的组成元素不同而已。
如果一种文字系统想要用一个图像表达一个词, 比如汉字, 它就必须要是[+P, +S]这种类型, 即 前文提到的类型 (3)。 这样, 就形成了形, 音, 义之间的三角关系。 有些学者过于强调形与义的关系 而忽略形与音的关系, 尤其是在分析汉字的时候。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鲍则岳认为文字必须要有表音成分存在, 文字如果没有语音 就不能代表语言。 “表意文字 (ideograph)” 这一概念会让一些人误以为汉字不是记录语言的, 而 是表达思想的, 或者是表达概念的, 因此, 鲍则岳不使用 “表意文字 (ideograph)” 这一说法, 而将 汉字的性质定为 “表词文字 (logograph, lexigraph)”。 将汉字定性为 “表词文字”, 不仅可以避免 “表意文字” 容易造成的两种困惑, 同时也可以凸显鲍则岳的“所有的文字都必须要有表音成分的 存在”这一核心观点。
鲍则岳虽然将汉字定性为“表词文字”, 但是, 他也是承认 “汉字是表意文字” 这一论断的。 鲍 则岳对汉字性质的理解与中国学者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认为, 这种不同表现在:
第一, 鲍则岳承认汉字是表意文字, 但是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好像都不是为了证明这一论断, 而是更多着力于对“汉字是表达思想的”“汉字是表达概念的”这两种他认为西方学界普遍存在的 错误看法的驳斥。
第二, 鲍则岳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文字记录语言的层次问题, 无非是要证明 “汉字是记录汉语 的词的”, 并进而得出 “汉字必须表音”, 因为每一个词都必须要有音。 这里, 他还顺带着批评了一 些学者过于强调汉字的形与义的关系而忽略形与音的关系。 他的矛头可能是指向一些中国学者的, 因 为 “因形求义” “据义析形” 一直都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 究确实会给人一种重视形义关系而轻视形音关系的印象, 但是, 我们认为, 说中国学者 “强调形义 关系” 是事实, 说他们 “忽略形音关系” 则不是完全客观。 比如说, 由于古音学研究的蔚为大观, 很 多清代学者对汉字的形音关系的认识其实是很明确的, 段玉裁在 ≪广雅疏证·序≫4)中所说的汉 字的形音义 “三者互相求” 和 “古形, 今形, 古音, 今音, 古义, 今义” “六者互相求” 的研究方法就 是很好的证明。 只不过, 中国学者更加注重的是汉字的形音关系在探求汉字的意义方面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 将形与音直接联系起来给汉字定性则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而已。
第三, 关于字与词的关系, 鲍则岳认为, 文字是记录词的, 而词既有声音也有意义, 所以文字不 能只记录意义不记录声音。5) 也就是说, 鲍则岳的关注点在于文字的记词职能, 是文字的功能。 我们认为, 中国学者一般倾向于将“字”和“词”作为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处理, 文字的本体是字形, 文 字的功能不能等同于它的本体。 一方面,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文字的产生, 发展, 演 变都要受到语言的影响, 但是文字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事项, 也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演变规律, 并在 一定程度上对语言的发展和应用也有影响。 比如, 王宁先生在论述汉字和汉语的关系时说:“汉字 直接参与了汉语的造词过程, 所以, 汉语单音词或语素的区分和新词的标志大部分已经不是声音, 而是书写形式——字形。 当我们想弄清一些相关的意义是一个词的不同义项还是已经分化为不同的 词时, 一般要看是否造了新字。”6) 另外, “就两种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而言, 它们既是语言的载体, 音和义又是密不可分的语言的两大要素, 当然同时记录了语言的音和义。 表音文字绝非只记录音 而与义无关, 表意文字也不是只记录义而与声音无关。 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 表意文字和表 音文字并无区别。 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一样, 它的符号都是和整个词发生关系, 只是它们连接词的 纽带有的是语音, 有的是意义而已。”7) 因此, 王宁先生在沿用“表意文字”这一概念的同时, 也提出 了“构意文字”的概念:“为了不把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和它构形的依据混淆, 更准确的称谓应当说, 英文是拼音文字, 汉字是构意文字。”11)
Ⅲ. 汉字的起源
1. 对有关汉字起源的传说的认识
和很多学者讨论文字的起源都会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开始谈起一样, 鲍则岳也认为, 在现 代意义上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一理解出现以前, 人类对文字的认识都是 “上帝 创制” 或者 “某些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创制” 这种形式的。 从世界范围内来说, 每个民族的认识又 略有不同, 比如古代巴比伦强调的是“文字与人的命运, 人的未来之间的联系”, 古代埃及和古代印 度关注的是文字在解释 “各种事物在世界中存在与运行的秩序” 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唯一的例外 可能就是古希腊了, 古希腊从一开始就将文字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 而与神话传说人物无关。
鲍则岳将有关汉字起源的传说分为两种, 一种与 “仓颉” 有关, 一种与“伏羲”有关。
1) 仓颉造字说
鲍则岳通过对记录汉字起源的传说的文本分析得出, ≪荀子≫中关于仓颉的记录表明, 并不是仓 颉创制了汉字, 仓颉只是与“创制汉字”这件事情有关, 只不过他是唯一被记录下来传至后世的人名, 而仓颉得以流传的原因就是 ≪荀子≫所说的“好书者众矣, 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到了 ≪吕氏春秋≫ 和 ≪淮南子≫, 就径直将仓颉说成是汉字的创制者了, 高诱的注更是为这种说法蒙上了一层神秘 的色彩。 鲍则岳引用Seidel的分析认为, 仓颉造字使得鬼神的力量可以得到节制, 从而出现了“天雨 粟, 鬼夜哭”的情况。 对于这种神秘现象的出现, 王充 ≪论衡≫已经否认了与仓颉造字的关系。
总体来说, 鲍则岳对 “仓颉造字” 说的看法与目前中国学者的主流看法是一致的, 即, 并不是仓 颉一个人创造了汉字, 他很可能只是一个在造字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或组织者。 但是, 鲍则岳对 ≪荀子≫中的记录的理解可能有一点问题。 ≪荀子≫ “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这句话, 根 据 ≪玉篇≫的解释, “壹” 是 “聚也, 合也” 的意思, 这和鲍则岳所说的仓颉是 “唯一被记录下来传至 后世的人名” 这种说法并不一样, “聚也, 合也” 的意义更突出了仓颉是一个主持者, 组织者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句话断句为“好书者众矣, 而仓颉独传者, 壹也”可能更好理解仓颉的角色。
另外, 鲍则岳提到高诱注中“鬼”的异文有作 “兔” 的, 据此, “鬼夜哭” 可能是 “兔夜哭”, 而 “兔夜哭” 的原因是害怕自己的软毛被拔掉制作毛笔以及由此带给自己的伤害。 这种利用古书异 文来重新认识一个问题的做法既有趣又新颖, 值得我们在关注类似问题时借鉴。 但是, 我们也要 看到, 这种做法也有一定的问题:第一, 比如说, “兔夜哭” 的解释合情合理, “兔夜哭” 与 “天雨 粟” 的关系是什么就不太好解释了;第二, 如果二者没有关系, 各种文献中将二者并列的原因又 是什么也不容易说清楚;第三, “鬼” 写成 “兔” 这种异文现象常见与否, 是不是只有这一个文献 例证, 用 “孤证” 来解释文献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2) 伏羲造字说
“伏羲造字” 的说法在汉代以及汉代之前的文本中都是没有的, 伏羲一般是被描述为 “始作八卦” “作结绳” 等一些发明, 这种描述最早出现在 ≪易·系辞≫中。 到了许慎 ≪说文解字·叙≫将 “伏羲” 和 “仓颉”联系起来, 也就将“八卦” “结绳” 与 “造字” 联系了起来, 从此以后的各种论述中它们便 形影相随不可分离了。 但是汉代以后, “仓颉造字” 说明显式微, “伏羲造字” 说明显流行开来。 这一 流行和道教的发展关系密切, 其结果便是 “太上老君造字” 说逐渐超越了 “伏羲造字” 说, 伏羲仅 仅成了引入这一说法的途径而已。
这里, 鲍则岳没有继续往下说的是, “太上老君造字” 说又是怎么样让位于我们现在更熟悉的 “仓颉造字” 说的呢?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道家的影响虽然日渐扩大, 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儒家思想才是意识形态, 是当时最深层, 最根本的社会思想, 从这个角度来说, “太上老君造字” 说的影响也只能是有限的, 不 会一直占据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当然, 这一看法可能也有问题, 因为仓颉的确更 多的出现在道教的画像和雕像中。 那么, 同样都属于道教系统, “太上老君造字” 说的流行可能主要 得益于李唐王朝的推动和后续影响, 而当李唐王朝覆灭后, 这种推动力没有了, 影响也就逐渐式 微, 这个时候, “仓颉造字” 说又得以重新流行。
第二, ≪说文解字≫是传统小学的根本之作, 其影响力不容忽视。 也就是说, 小学家也好, 普 通读书人也好, 甚至是社会上的一般民众, 他们对 “文字” 的认识基本都是以 ≪说文≫为起点的。 而在 “汉字的起源” 这一问题上, ≪说文叙≫ “仓颉造字”的说法也会随着汉代以后对 ≪说文≫的 研究越来越深入而传播得越来越广, 进而完全超越 “太上老君造字” 说。
2. 对汉字起源的认识
鲍则岳将圣书字, 楔形文字, 汉字这世界文字的三大起源放在一起讨论, 批评了 “汉字起源于 中东地区, 而后传入中国” 的西方流行观念。 他认为, 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早已经用大量 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说法的错误。 他自己也非常明确地表示认可汉字是自源文字, 中国, 埃及和美 索不达米亚三地发明文字的机制是一样的, 即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 “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的 整个人类都普遍使用的方式。
但是, 鲍则岳也认为, 从图画到文字并不是人类所有文字产生的唯一方式。 这里鲍则岳引用的 主要是白瑟拉托 (Schmandt-Besserat)有关“文字起源于陶筹”的研究。
不可否认, 白瑟拉托的观点中有一个明显的弱点, 比如, 她认为“五” (five)或者 “五只羊” (five sheep)的概念与记录这些概念的书写符号是同时产生的。 事实上, 应当是先有了 “five” 或 “five sheep” 的概念, 然后才能产生记录这些概念的书写符号。
鲍则岳认为, “象形文字的先导 (pictographic precursor)” 是只有意义没有声音的 ([-P, +S]), 只 有当它有了声音, 变成[+P, +S], 才能认为它是文字。 正是从无声音[-P]到有声音[+P]的转变标志 着从非文字到文字的转变, 能证明这种转变的象形文字的例子并不是十分明晰, 白瑟拉托的证据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转变, 但它是非象形文字方面的证据。 这就说明, 我们普遍认为的所谓 “象形文字的先导 (pictographic forerunners)” 可能并不是文字产生的唯一来源和唯一机制。
但是, 除了拱玉书, 何丹等少数几位学者十分推崇白瑟拉托的 “文字起源于陶筹说”, 大多数中国 学者都是十分认同“汉字起源于图画”这一论断的。 针对有关汉字起源的各种说法, 我们的观点如下:
首先, 对于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 白瑟拉托的观点尽管为理解人类文字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全新 的认识角度, 但是, 楔形文字和汉字毕竟不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字系统。 楔形文字的特殊起源方式 和它所存在的时间, 地点和特殊的文字形制都有密切关系, 而汉字在这些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性, 适用于楔形文字的起源方式不一定适用于汉字。
其次, 无论是图画还是陶筹, 从本质上来说, 都可以理解为一种符号, 二者的差别在于表达意 义时抽象程度的不同, 和陶筹相比, 图画具象性更多一些。 不过, 按照白氏的说法, 其实初期的陶 筹也是对陶罐中实物的具体描绘, 后来陶筹抽象性逐渐增强, 变成了单纯代表陶罐内实物的简单 符号。 很多中国的文字学者, 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也认为, 那些刻画在新石器时代器物上的符号 也是图画或其他实物逐步抽象的结果, 继续发展下去就产生了汉字, 只不过由于材料的缺乏, 从 这些符号到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之间的链条无法完整地续接上而已。
最后, 鲍则岳认为, 一种“前文字”阶段的符号变为真正的文字的标志是声音的出现, 即这种符 号从[-P, +S]变成[+P, +S]。 但是, 鲍则岳认为这种转变是 “突然的” “瞬间完成的”。 对于这一点, 我们认为, 探讨 “汉字起源” 问题应该区分 “符号个体” 和 “符号总体” 两个方面:单个的符号从 [-P]到[+P]的转变应该是突然的, 瞬间完成的, 但是对于一个个体数量众多的符号系统而言, 还是 要有一个长时间的量变的过程才能达到质变。
Ⅳ. 汉字的发展阶段
鲍则岳将汉字的整个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图画文字阶段 (the zodiographic stage), 字符多价 阶段 (the stage of graphic multivalence), 语义/语音限定成分阶段 (the stage of S/P determinatives)。 下面分别来看。
1. 图画文字阶段 (the zodiographic stage)
有些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指出, 甲骨文中的一个符号可能代表了一种礼仪行为或祭祀行为。 这类 符号算不算文字?鲍则岳认为, 首先要确定它们是不是有明确的发音, 如果有, 即使一个符号的发 音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短语 (笔者注:即比“词”的单位大)也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文字, 如果没有, 则不能认为它是文字。 尽管甲骨文中存在着“合文”现象, 但是绝大多数甲骨文的符号都是语标文 字 (logograph), 即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词。
可以看出, 鲍则岳在不停地强调“[+P]”的根本重要性。 他引用Iversen (1961)的观点, 指出Iversen 所使用的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 “realized (意识到)”, 绘画艺术与真正的文字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这种 “意识 (realization)”。 当一个图形或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物体本身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 “文字画 (pictograph)”, 并且可以认为它们是文字的先声。 当人们意识到一个图形或者符号不止能代表一个物体本身, 而是可 以代表这个物体的 “名称 (name)” 时, 这种符号就是文字了, 就可以称之为 “图画文字 (zodiograph)”。
文字画与图画文字在形式上可能是一样的, 但在功能上具有本质的区别。 由于图画文字是表词 的, 所以它们是语标文字。 又因它们是直接表事物的, 所以可以认为图画文字是最早的语标文字 类型之一。 套用一个数学上的概念就是, 图画文字是语标文字的一个 “子集 (subset)”, 即所有的 图画文字都是语标文字, 但不是所有的语标文字都是图画文字。
那么, 文字画与图画文字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从文字画到图画文字的转变又是怎么完成的呢?鲍 则岳指出, 文字画与图画文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能表“词”, 从文字画到图画文字的转变也就是 从前文字阶段到真正的文字的转变, 这一转变是通过“约定俗成 (conventionalization)” 实现的。 文 字画是表事物的, 这种象形角色要求它要易辨识, 并且尽量真实地反映所代表的事物。 当一个符 号是表词的, 由于词是没有视觉形式的, 所以符号和事物之间的紧密结合需要靠语言 (声音)来说 明, “对语言的符号反映 (the graphic reflection of speech)” 就可以不用完全写实。
符号的约定俗成在楔形文字和甲骨文的发展中都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这一点上, 埃及的圣书字 是一个例外, 尽管如此, 埃及的圣书字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约定俗成”的。 比如, 尽管圣书字没有实 施符号的 “去描写性” (笔者注:鲍则岳这里所说的“去描写性”是指中国学者所说的 “减少象形性”), 但是圣书字确实规范了符号的外形, 也在标音符号与其他符号配合使用方面加强了系统性。
无论如何, “约定俗成” 都是从文字画到图画文字的转变过程中的表面现象和附带产品, 这一 转变的根本特征是, 符号究竟是表事物的还是表词的。 即, 我们理解一个符号, 是因为理解了它 所代表的事物, 还是因为我们理解了它所传达的词义。
从以上的论述, 可以非常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在文字起源时, 没有任何规定说符号只能表达思 想。 这样, 鲍则岳就回到之前批评 “表意文字” 这个概念时的论断, 认为无论是汉字, 楔形文字还是 圣书字, 使用 “语标文字 (logograph)” 或 “表词文字 (lexigraph)” 这样的术语来指称是更加合适的。
2. 字符多价 (graphic multivalence)8)阶段
从画出某个具体事物到用一个符号代表这个事物, 这种转变是一种进步, 但是对记录语言来说 这仍然是一种非常初步的方法。 很快人们就意识到, 即使用来记录最简单的抽象事物, 这种方法 也是不能做到的, 更不用说记录实际语言中的那些拥有多种意义的复杂事物了。 仅仅有记录具体 事物的图画文字是不能称之为 “文字系统” 的, 图画文字的这种受限性, 迫使人类去思考如何去记 录那些无形可象的事物。 在这一点上, 古代的中国人, 苏美尔人和埃及人面对同样的问题, 几乎选 择了同样的应对措施, 那就是, 人们发现图画文字可以衍生出两种用法:表音和表义。
图画文字既然是文字, 就有形有音有义, 形是文字的本体, 音和义是语言赋予文字的。 既然这 样, 那么可不可以在音和义两个角度寻找突破?顺着这个思路, 人们发现, 可以用A字的字形和字 音相结合而不管A字的意义这种方法来表达B, 这就是同音借用;也可以用A字的字形和字义相 结合而不管A字的读音这种方法来表达C, 这就是同 (近)义借用。
1) 同音借用
尽管是同音借用, 借字仍然是既有音又有义的 ([+P, +S]), 所以借字仍然是语标文字。 这是因为, 尽管借字所表达的词和它作本字时所表达的词不一样, 但它仍然是表词的。 这一观点可以表述为:
从理论上说, 一个字符的原始语音可以用来表达任意数量的同音或近音的不同意义的词, 因 而上面的公式也可以写作 “G:[+P, +S₀, +S₁, +S₂ ... +Sn]”。 S0代表字源义, S₁到Sn代表在同 音的基础上某个字符所有的另外的意义, 从理论上说, n可以是无穷的。 但是, 在现实使用中, n的 值超过三的情况非常少见。 人们不会在自己的语言中过度使用同音借用, 因为只要是同音就会有 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这种模糊性会影响语言的交际功能, 使交际功能的精确性下降。 所以人们会 限制同音的使用量, 这就进而限制了记录同音词的文字的使用量。
这种同音借用的“多义字 (a graph which is used in a polysemous way)”的使用具有两个重大的 意义:一是可以为无形可象的抽象事物造字;二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已有字符, 这样既增强了 交际的经济性, 又可以在这些字的基础上大量增殖新字。 比如“象”这个字形 (G), 读音为xiang (P), 既可以表示“大象” (S₀), 也可以表示“图像, 幻象” (S₁)。
2) 同义借用
这种用法的要求是, 一个字符所记录的几个词在意义上相同 (相近或相关), 而这几个词的读 音不同。 这一观点可以表述为:
比如“口”字, 在古文字阶段, 它既可以表示 “口 (mouth, 嘴巴或者其他物体的开口)”, 也可以 表示 “名 (call or name, 称呼, 命名)”, 这两个意义是相关的, 都用 “口” 这个字形, 但是在表示第 一个意义时读音为kou, 在表示第二个意义时读音为ming。
但是这种同义 (相近或相关)而多音的用法在今文字阶段表现并不明显。 我们认为, 这主要是 因为, 在后来的文字发展过程中, 人们在原字形的基础上增加了构件, 将这些相关的各个义项分 化出来, 并且给每个义项一个特定的读音, 以区别于其他义项, 这就掩盖了早期文字中字符的 “同 义借用” 现象。
从理论上说, 一个字符如果记录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这些词之间要么读音相同意义无关, 要么意义相关读音不同, 要么读音和意义都有关。 读音和意义都完全无关而字形相同的情况如果 存在, 也是两个在来源上就完全不一样的字符偶然选择了同一种形式来记录。 比如 “谷”, 既可以表 示 “山谷 (valley)”, 读音为gu, 也可以表示 “匈奴统治阶级中的一种头衔 (part of a titular designation within the Hsiung-nu hierarchy)”, 读音为lu。
多义字和多音字的使用虽然都在提高文字的使用效率和增强文字的表达功能上有益处, 但是它 们也会给文字的使用增加模糊性。 为了减少这种模糊性给交际带来的麻烦, 在后来的文字发展过程 中, 人们采取了两种相应的措施:一是固定读音, 二是通过在原字形基础上增加不同的构件或者新 造字形的方法来表达不同的词义。 尤其是, 当人们意识到, 增加语义限定成分来减少语义模糊性可 以作为一种普遍方式用来造字, 这才使得汉字从“字符多价阶段”发展到了“限定成分阶段”。
3. 限定成分阶段 (the stage of S/P determinatives)
限定成分有两种, 即 “语义限定成分 (semantic determinative)” 和 “语音限定成分 (phonetic determinative)”。
“语义限定成分” 是指在源字符的基础上增加的另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的功能是限定源字符的语 义模糊性 (the second graph appended to the original is meant to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a semantically ambiguous graph)。 语义限定成分是附加上去的 (auxiliary), 也是不发音的 (aphonic)。 源字符在增 加语义限定成分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 “复合字符” (compound graph), 这个复合字符就可以用来记 录包含两个甚至更多意义的源字符中的某个意义。
比如, “勿” 是一个 “源字符”, 有 “物体, 事物” 和 “不要”两个意义, 增加一个字符 “牛” 后, “物” 这个复合字符代表“物体, 事物”这个意义, “勿” 只用来代表 “不要” 的意义。
“语义限定成分” 有时也称 “义旁 (semantic classifiers)”, 也有很多人将称作 “词根”。 但是 “语 义限定成分” 和 “词根 (radical)” 是不能完全等同的, 尽管两者在有些时候会有交叉。
解决语音的模糊性问题的做法与此类似。
“语音限定成分” 是指在源字符的基础上增加的另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的功能是限制源字符的 语音模糊性。 这个附加上去的字符只在语音上起作用, 而不用考虑其意义 (尽管有时候这个字符 的意义和源字符也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 “口” 是一个源字符, 有 “嘴巴, 开口” 和 “称呼, 命名” 两个意义, 有 “kou” 和 “ming” 两个读音。 增加一个字符 “夕 (月)” 构成复合字符 “名”, 读音为ming, 源字符 “口” 只读音为kou。
鲍则岳认为, 只有出现了语音限定成分, 一种文字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我们认为, 鲍则岳对“限定成分”的表述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 汉字, 尤其是现代汉字, 可能包含三个, 四个, 五个甚至六个构件, 对于这些汉字来说, “增 加限定成分” 的过程和只有两个构件的汉字的构成过程是一样的, 即, 在这些多构件的汉字中 “增加 限定成分”是逐层实现的, 也就是说, “增加限定成分” 这一操作具有 “递归性 (the “add determinative” operation was recursive)”。
仍以前面所举的“名”为例, 当我们需要将“铭记, 铭刻”这个意思从源字符“名”中分化出来时, 就添加“金”这个限定成分来构成复合字符“铭”。
从理论上说, “增加限定成分”操作的“递归性”可以是无限的, 但是, 人们并不会无限使用这种 递归性, 因为一旦某个字的构件超过五个就会使它看起来十分地笨拙且难用。 另一方面, 增加限 定成分也不完全都是为了使意义或声音更加精确, 有时人们为某个字增加限定成分仅仅是出于审 美需要, 使这个字看起来在结构上更加平衡和美观。
第二, 由于为某个字符增加语义限定成分使人感受到的影响太过强大, 以至于为某个字符增加纯 粹表音而不表义的限定成分这种做法似乎从未发生过。 究其原因, 早期汉字的音义联系实在过于紧 密, 后来这种联系的紧密性又不断得到加强, 即使是在将某个字符用为语音限定成分时也是如此。 因为作为语音限定成分的字符本身就是可以独立表达一个词的, 即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这种意义即 使在它仅仅履行表音职能时也不会被抹去。 甚至可以这样说, “语音限定成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同时 也是潜在的语义限定成分 (phonetic determinatives are in a sense latent semantic determinatives at the same time)”。
第三, 所有的汉字都是有音的, 没有读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 独体的图画文字既有音又有义, 有 时它的音义还不止一个。 由两个或者更多构件构成的字, 其中至少有一个构件必须是音符, 有时源 字符是音符, 有时附加的语音限定成分是音符。 如果由两个或多个构件构成的汉字, 其中的每个构 件看上去都不表音, “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其中的表音成分, 而不是这个字没有表音成分”。
Ⅴ. “六书”与 ≪说文解字≫
无论是谈论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性质还是汉字的发展, ≪说文解字≫都是无法绕过的。 鲍则岳 首先梳理了“六书”从首次出现到拥有完备解释的发展过程, 即:
郑众 ≪周礼·保氏≫注:“象形, 会意, 转注, 处事, 假借, 谐声”
↓
班固 ≪汉书·艺文志≫:“象形, 象事, 象意, 象声, 转注, 假借”
↓
许慎 ≪说文解字·叙≫:“指事, 象形, 形声, 会意, 转注, 假借”
按照裘锡圭先生的说法, “上引这三家的 ‘六书说’ 应该是同出一源的”, 因为:第一, 郑众是郑 兴的儿子, 郑兴是刘歆的学生;第二, 班固 ≪汉书·艺文志≫是在刘歆 ≪七略≫的基础上编成的; 第三, 许慎是贾逵的学生, 而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刘歆的学生。9)
鲍则岳指出, “六书” 不是要解释汉字的发展过程, 而是一种 “对汉代已经存在的汉字进行分 析和归类的尝试”, 即, “六书” 是一种共时描写而不是历时分析。 这种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 秦以来对汉字进行规范的影响, 也受到了汉代的世界观的影响 (笔者注:比如对各种与 “六” 有关 的事物的认识)。 鲍则岳对 “六书” 的认识与戴震等学者的 “四体二用” 说分类相同, 即 “指事, 象 形, 形声, 会意” 为一类, 是分析汉字的内部结构的, “转注, 假借”为一类, 是分析汉字的使用的。
鲍则岳认为 “六书” 中问题最大, 争议最多的是“会意”。 除了例字 “信” 的 “从人从言” 可以有 多种解释之外, 至少还有三个方面令人怀疑:
第一, 班固是将 “会意” 说成 “象意” 的, “象意” 没有 “会合两个 (或多个)字的意义” 这种意思。 第二, 从起源上讲, 任何一个字里面都必须有声符, 单纯地 “会合其意” 是不存在的。 第三, 从文字 系统的角度来说, 符号在表词时只体现其会意价值而不体现其标音价值的做法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通过对 “言” 的古音分析, 鲍则岳认为许慎所谓的 “形声” 和 “会意”不是相互排斥的。 即, 从 历史事实上来说, “信” 应该是个形声字, 而从许慎的分析系统来说, “信” 可以是个会意字。 在坚 持 “一个字必须有表音成分” 的原则下, 鲍则岳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要找出为什么一个形声字同时 也可以是会意字。10)
关于 ≪说文解字≫, 鲍则岳先是提到 ≪说文≫从完成 (公元100年)到献给汉安帝 (公元121年) 这中间存在长达21年的时间差问题。 他认为许慎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许慎想要在完 成初稿的基础上继续打磨以使它更加完善, 二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也迫使许慎最好这样做。
从政治环境上来说, 公元121年汉安帝即位, 结束了窦, 邓两大集团为代表的势力对皇权的威胁, 使得统治权重回皇帝之手, 安帝下令, 希望学者们为皇家服务。 许慎已经完成的 ≪说文≫遇到了 一个合适的时机。
从学术环境上来说, 一般都认为许慎是一位古文经学者, 这在今文经学者当道时是不容易打开 学术局面的。 鲍则岳引用米勒 (Miller)的观点, 认为其实许慎在他的 “古文经学者集团” 里是保持 着显著的独立性的 (holding remarkably independent views within his group)。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是, 许慎不止是要写一本字典或者文字学著作, 他更希望的是以此为手段, 实现“文字者, 经义 之本, 王政之始”的目的。
除此之外, 许慎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受到了秦以来 “书同文字, 统一度量衡” 等行为所带来的系 统化, 标准化精神的影响, 还有就是自秦至汉初一直盛行的 “大一统思想” (Vereinheitlichungsgeis t)11)附带的 “阴阳五行” 理论。
鲍则岳认为, 许慎虽然将其书命名为 ≪说文解字≫, 但是它的 “文” 和 “字” 并没有在行文中 明确指出, “文” 是作为 “部首” 存在的, ≪说文≫全书的基础其实是 “六书” 理论。
“指事” 和 “象形”两书用来表述独体字, 因而只能 “说” 不能 “解”。 鲍则岳充分肯定了许慎对“形 声” 的说解用语 “A, B也, 从X, Y声” 中专门提及 “声” 的重要意义, 这标志着许慎明确宣布构件“Y” 是用来确定 “A” 的读音的。 这种肯定仍然建立在对 “字符中必须有表音成分存在” 的基础之上。
不过, 我们认为, 对于 “字符中必须有表音成分存在” 这一点的坚持, 既显示了鲍则岳的理论系 统性与一惯性, 但是也可能给人一种他带着 “印欧语眼光” 看问题的印象。 因为, 很多研究都已经 表明, 在许慎的时代, 形声字已经占汉字总字数的大多数, 对形声字的分析强调 “Y声” 是必然的。
最后, 鲍则岳还分析了 ≪说文≫一些解说格式的变体 (“从XY” “从X从Y, Y亦声”)产生的原 因, 分析了 “读若” “小篆和大篆, 籀文, 奇字的关系” “≪说文≫的字数与新附字” 等问题。
Ⅵ. 汉字的拼音化问题
鲍则岳对汉字拼音化问题的讨论, 是以汉字在秦汉时期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为切入点的, 而他所 用的材料主要是马王堆汉墓帛书。 从鲍则岳所举的例证中可以看出, 汉代之前的汉字中, 表义构 件还只是少量存在的。 到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中, 汉字的表义构件开始大量出现, 但是这种表义构 件往往具有随意性和多样性。 这种现象表明, 汉字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出现向表音或者说 “去语义化” 发展的趋势。
比如, 本义为 “钩子” 的 “句” 这一字形, 经常用来记录 “后来” 的 “後”, “王后” 的 “后”, “苟 且” 的 “苟” 三个词。 当 “句” 这样一个字形用来记录 “後 (*gugx)” “后 (*gugx’s)” “苟 (*kugx)” 这几个读音相同相似的词时, “句”就趋向于逐渐淡化表义功能, 这使得“句”看上去更像是代表了这 三个词的语音而不是其意义。 如果这种趋势发展到极致, 人们就可以有意识地, 精确地用 “句” 来 代表*gugx, *gugx’s, *kugx这三个读音而不管词的意义。 这样, “句”就不再是一个表意文字, 而变 成了一个纯粹的表音文字。12)
同音借用现象是战国时期文字的重要特征。 汉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字符多价” 阶段)所产 生的字,到了第三个阶段 (“限定成分” 阶段)依然可以被同音借用, 只有在可能产生语义模糊性的 情况之下才会增加限定成分。 这种 “走回头路” 的方式, 在同音借用字与增加限定成分的字两者 保持平衡的情况之下是可行的。 但是, 马王堆帛书的用字情况表明, 它们有意偏离这种平衡状态, 而 更明显地走向了同音借用的道路。 这种趋势如果不加纠正, 可以想见, 出现纯粹表音文字的情况 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如果一种文字体系中的大多数字都发生同音借用的现象, 发明一种只用来表音而完全不表义的 文字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 马王堆帛书中的文字基本上还是既表音又表义的 ([+P, +S]), 但其中一 些字已经差不多是只表音不表义了 ([+P, -S]), 而更多的字则是表义特征已经非常不稳定和弱化了。
鲍则岳认为, 汉字没有从第三阶段继续向前发展为第四阶段的表音文字, 最重要的原因是: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发号系统, 汉字处于“限定成分”阶段时的汉语仍然是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 的语言, 这就使得任何一个汉语的音节都是带有意义的。 既然每一个音节都带有意义, 那么记录 每个音节的字符就天然且自动地带有意义, 进一步, 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一种只记录汉语的语音而 完全不顾及汉语的意义的书写符号系统。
虽然在汉字的第三阶段时, 汉语词是以单音节为主的, 但是后来的汉语词已经变为以双音节 词为主了。 有的学者 (比如George Kennedy)甚至认为, 汉语从东周时期开始就已经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单音节语言了, 有许多词已经是只能看作双音节的了。 卜弼德 (Peter A. Boodberg, 1937)认为发 生这种转变的主要机制是汉语单音节词中的复辅音或辅音群断开13), 每个辅音后面又因为发音的 需要而带上了元音。
以 “痀偻” 为例, 最早的书写形式是 “偻 (*kljugx)”, 辅音断开之后变成了*kjug-ljugx, 写成了 “痀偻”, 这里的 “痀” (或者其中的 “句”)是完全可以只表音不表义的。 如果这种趋势一直且大规模 发展下去, 就完全可以产生很多只表音不表义的文字, 进而导致整个文字系统变为表音体系的。 但是汉字系统具有强大的表义倾向, 所以, 后来专门给 “句” 加上了 “疒” 以强化其表义功能。 这是 为什么呢?米勒 (Miller)的解释是这样的:中国的语言学传统从产生到发展都与中国人的世界观有 着巨大的联系, 尤其是中国人的观念中对道德问题, 对人类社会, 对宇宙秩序的认识。 米勒认为, 在这 种认识的基础上, 中国人会把“秩序”看得无比重要, 人自身, 人所处的社会以及宇宙自身因此变成不 仅是学术探究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 这三者反映了或者可以归结为什么样的 “合理的, 具有道德适 应性的, 严格的秩序”, 这种秩序如何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里体现出来。 吉德炜 (David Keightley)对 此类观点有进一步阐释。 他们都认为, 对 “秩序” 的推崇影响了中国人对语言相关问题的态度, 就是 特别重视 “合适的意义” 与“合适的功能”。14)
米勒认为, 中国人在区别语言和记录语言的文字二者时没有任何困难, 中国人对一个字的理解是 同时理解其形音义的。 卜弼德也认为, 中国人具有高度的“协同一致性 (synethological congruence)”或 者叫 “适应性 (appropriateness)”。
在这种情况下, 汉字出现的纯粹表音倾向和 “去语义化” 倾向就不可能无限发展下去, 对汉字 进行标准化, 系统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即重新强化汉字的 “形-声-义” 三者之间的关系。 强化的结 果就是, 尽量使每一个汉字都是记录词的, 也就是同时记录意义和声音。 所以, 对古时的中国人来 说, 根本不会想到声音和意义是一个字所具有的两种各自独立, 可以分开的特性。
Ⅶ. 结 论15)
鲍则岳拥有比较广阔的比较文字学的视野, 在讨论有关汉字的每一个方面的问题时, 都能做到 将汉字与圣书字, 楔形文字进行对比研究。 鲍则岳认为汉字是自源文字, 汉字起源于图画, 从 “前 文字” 到 “文字” 的转变是一个突变的, 瞬间完成的过程, 汉字在进入 “文字” 阶段之后经历了从 “图画文字阶段” 到 “字符多价阶段” 再到 “语音/语义限定成分阶段” 三个发展阶段。 同时, 无论 是讨论汉字的起源, 还是将汉字定性为 “表词文字”, 还是梳理汉字的发展阶段, 鲍则岳都一以贯 之地坚持了他的 “每一个汉字都必须有表音成分” 的大原则。 鲍则岳还谈到了汉字起源的相关传说, “六书” 与 ≪说文解字≫, 早期汉字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汉字拼音化等问题, 让我们看到他对汉字研 究领域的关注是全面的, 也是具体的。
总之, 正如鲍则岳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 对于汉字的认识, 可以有 “材料” 和 “语言学” 两个角度。 从 “材料” 的角度来认识, 主要是将文字看作一种物体, 即主要关注它的 “外在表现”, 比 如文字形体的演变, 形体会受到哪些材料的影响, 文字书写过程中运用了哪些方法以及不同文字 形态的艺术特点等。 从 “语言学” 的角度来认识, 即认识一个书写符号的 “内在历史”, 也就是说, 要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出发来解释文字的起源与演变, 这种文字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它通过何种 操作来发挥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一首要作用。 鲍则岳本书出版于1994年, 他当时认 为, 以裘锡圭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也是从外部特征方面来考察汉字的, 而他自己更注重从内部 角度考察汉字。 在本书的序言中, 鲍则岳就申明了写作此书的两个目的:第一, 关于汉字的性质, 在西方社会存在着广泛传播的神秘说法和一些经常混淆的学术概念, 他要对这些神秘的说法和混 淆的概念进行尽量的厘清。 第二, 通过对汉字的起源和汉字的发展过程两个方面的思考和讨论, 让 人们更好地去理解汉字的形式与功能。 正如夏含夷所说:“在此书的序言里,鲍则岳说他将要写一种 ‘内在语言学史’, 也就是不去管文字怎样代表口头语言以外的问题, 诸如文字的媒介和社会环境”16) 也就是说, 鲍则岳和中国学者的研究角度, 研究目的是不同的。 鲍则岳的研究角度是文字的 “内 在历史”, 是文字的功能, 目的是纠正西方人对汉字的一些错误看法, 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汉字; 中国学者的研究角度是文字的形体, 是将形体作为文字的本体, 目的是将汉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来研究, 并且尽量避免它与音韵学, 训诂学或其他语言学领域的纠葛。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 鲍则岳对汉字学研究领域的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深入思 考, 很多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也值得我们借鉴或者进一步讨论。 限于水平, 加上由英语译为汉语的 过程中理解错误等因素, 本文对鲍则岳的汉字学研究的介绍和评价肯定有许多不当之处, 恳请得 到指正与批评。